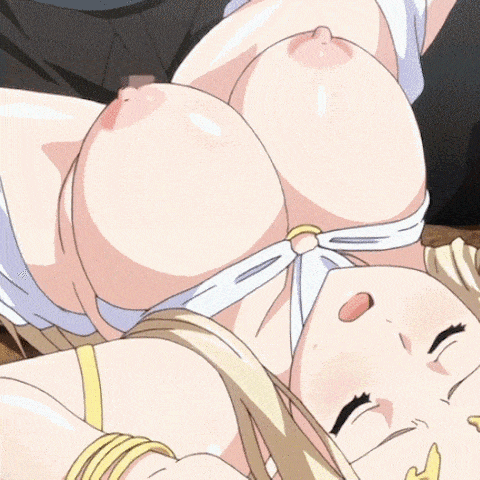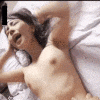第三章
十三年前,王庭。
西北吹来的寒风仿佛凶猛咆哮的野兽,吹过帐上悬挂的车轮,这是逐水草而居的匈奴人不可或缺的工具,季节更替之时,这些木制的车轮可以帮助整个部落以最快的速度迁徙。狂风在帐外盘桓,让篝火的火焰都变得孱弱,但剥下来的兽皮硝制而成的帐篷挡住了狂风和寒冷,燃烧着的炉火让帐内温暖如春。
拓跋烽看着长几上的字,少年说,这是“拓跋烽”。
他拧着眉头道:“这么多道,谁学得会?”
少年似有得意,说:“我啊,我学得会。”
拓跋烽点点自己的名字,不满道:“你知道我的名字,可我还不知道你的呢。难道这就是你们汉人的规矩?”
少年听了,显得有些为难。
他虽然住在王庭,可身份实在特殊。阿苏大单于厌恶南夏人,厌恶他们的礼仪、文化、规矩,可是在统治偌大的草原时又离不开他们的计谋和韬略,所以不得不把他的父亲留在王庭,可又不肯给他官职或者封赏,王庭中所有人都知道他的父亲是阿苏单于不可或缺的谋士,可没人真正尊敬他,他们认为他的父亲是南夏的叛徒。
也许拓跋烽也会这么想。
少年攥着毛笔,轻声道:“我叫景皎皎。”
他不怕拓跋烽笑话他的名字,因为他知道拓跋烽根本不明白“皎皎”的意思。
拓跋烽指了指宣纸上自己名字旁的空白,说:“写在这,我想看你的名字怎么写。”
景皎皎真的一笔一画地写下自己的名字。
在王庭中,很少有人在意他的姓名,人们只称他作“景大人的小子”,“景大人”听上去尊敬,其实是蔑称,不管谁来叫都充满讽刺,连阿苏单于都这么叫,叫他父亲“景大人”,更没人在意他。因为他和王庭中十六岁的少年们不一样,他们不是在摔跤,就是在射箭,或者骑马,没人理会一个成天只知道闷着头看那些拐七拐八的弯弯字的怪胎。
写完了,他把毛笔放回桌上,献宝似的推推宣纸,让拓跋烽看,“这是你的名字,这是我的名字,你看,都是三个字。”
他的手指一个字、一个字地点过两个人的名字,告诉拓跋烽这些字怎么念。
拓跋烽的目光却没有看字,而是盯着他的手指。
屏风上一闪而过的白得晃眼的手又浮现在他脑海之中,他看着墨字上景皎皎的手指,不由自主地抬起手,把自己的手也放在宣纸上,放在少年手边。他虽然只有十三岁,但从小就射箭、练武,还要干活儿,手很黑,也很粗糙,虎口和几根手指的指节处还生着厚厚的茧子,平日不觉得,现在放在景皎皎旁边,对比之下,简直惨不忍睹。
景皎皎愣了一下,说:“你的手,怎么这么多冻疮?”
拓跋烽动动手指,不以为然道:“天冷,当然会生冻疮。”
景皎皎把自己的手从宣纸上收回来,觉得有些羞耻。拓跋烽是拓跋部落单于的儿子,手都这副模样,相形之下,他简直活得不知好歹。可是,他不喜欢骑马,也不喜欢射箭,更不喜欢摔跤——没人会让他一起做那些,他父亲也不允许。
他攥紧自己的手,不想让拓跋烽看见。
拓跋烽不知道他想这么多,从靴中抽出一柄锋利的匕首,把那张宣纸一分为二,把写着“景皎皎”三个字的那一半折起来放到自己胸前的衣裳下,说:“我要在这待一个月,谁都不认识,你没事做,就教我读书吧,我也想知道为什么我阿爹这么喜欢南夏的东西。”
景皎皎睁大眼睛看着他,问:“你为什么要拿走我的名字?”
拓跋烽隔着衣裳拍拍那半张纸,不以为意道:“哦,我想拿我的,拿错了。没事,以后你教了我,我就不会认错了。”
景皎皎傻傻地看着桌上自己写的“拓跋烽”三个字。
这时,帐篷的门帘被从外面掀开,一个瘦高的男人走进来,看见帐中的拓跋烽,愣了一下。这人正是景皎皎的父亲景至丞,大单于阿苏身边既不受信任又无法抛弃的谋士。他是南夏人,在北燕为官,为匈奴所掳,在阿苏单于身边效力,半生跌宕,受尽折磨,不过四十出头,头发已花白。
拓跋烽“腾”的一下站起来。
景至丞认出拓跋烽,脸色微变,又挤出一个笑,说:“拓跋王子为何在此处?”
拓跋烽眼都不眨,说:“昆仑神的旨意,让我遇见你的儿子,我们聊得来,一定能做一生的好兄弟。”
景皎皎:“……”
景至丞脸色稍缓,点点头,语气温和地道:“你阿爹在找你。”
拓跋烽看看他,再看看景皎皎,对他道:“我明天来找你读书,你记得等我。”
他带着景皎皎的名字走了。
景至丞在长几的另一边坐下,给自己倒茶,看见宣纸上拓跋烽三个字,脸色有些阴沉。拓跋业和拓跋烽父子面见大单于时他也在旁边,看得出拓跋业对南夏、对中原人的好感,拓跋业也是匈奴人中少有的发自内
心地尊重他的部落首领,言谈之间,显得很欣赏他对大单于提出的一些建议。
可是……
景至丞攥着盛茶的碗,问:“你和他都聊什么了?”
景皎皎不想说,又不得不说:“他问我他的名字怎么写,告诉我他也想读书,想知道他父亲为什么那么喜欢南夏。”
景至丞的脸色更难看,长吁短叹一会儿,吩咐道:“他来找你,你固然不能拒绝,可也不要什么话都和他说。我知道你在此处交不到朋友,可你更不能把谁都当朋友。”
他压低声音,说:“我们不会永远留在这,爹一定会带你回南夏,到时候,不管你想和谁一起谈诗词、聊歌赋,都行。以你的才学,一定能在南夏结交无数文人墨客,为朝廷效力、加官晋爵也指日可待。”
景皎皎沉默地收起长几上让溅出来的茶水打湿的宣纸。
这些话,父亲说过不知多少次,要离开草原,要离开王庭,要离开匈奴,要回到北燕,要回到南夏,要回到中原。他听了太多、太多次,现在已做不出期盼的神情了。他知道父亲身在匈奴很痛苦,但更知道他的本质不过是一个懦夫,他没有那么深的谋略,他的无能才是他痛苦的最终来源。
景皎皎把宣纸夹在自己的书里。
曾经的北燕皇后兰氏含泪道:“我的孩子,你受苦了。”
夏侯烈挤出一个笑,说:“不过是献剑舞,有什么苦的。”
母子二人心知肚明,“剑舞”的真正含义究竟是什么,可谁都不忍说出口。这世上怎么可能还有比这更残忍的事,可他们又有什么选择。太原王府的宴饮和喧嚣仿佛离他们很远,可刺耳的声音萦绕不去。夏侯婴才不在乎当下的热闹从何而来,他只觉得自己的谋略天下无双,这些在他府上、和他觥筹交错的王公大臣们让他多年来积聚的郁气终于一扫而空,他已然能看见自己在丰都处处都是朋友的将来了。
夏侯婴知道侄儿终于回府,让人叫他过去。
兰氏惶惶地道:“这……”
夏侯烈道:“只是去饮酒,阿娘不用担心。”
是去饮酒,又不只是饮酒。
夏侯婴得意洋洋地和宾客们炫耀夏侯烈的脸蛋儿。
夏侯烈面无表情地坐在一边,一杯一杯地饮酒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