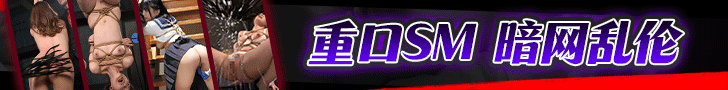这次出差去法兰克福,办完正事后,老板要我陪他去红灯区放松一下。
去就去吧。我个人没有那么高的道德底线,就算有也是约束自己,不会要求他人,更不能对发我工资的人评判什么。何况在这里性服务是合法经营,条件也规范,应该是没什么风险的。
老板姓徐,我们叫他徐总或老徐,同去的还有我同事苏谧,一行三个人。我进公司时间不长,虽然晋升很快,这里面当然有徐总对我特别赏识的缘故;苏谧跟随徐总有五六年了,对老板的习惯秉性更了解,不,应该说根本是了如指掌。
徐总家里有妻子,一个儿子在读大学,女儿读中学。那个女人我没见过几次;抛头露面的场合,徐总一般都带着苏谧。有时我真想说,苏谧就像徐总的小老婆。不过我也能理解,很多生意场上的活动是不能和女士分享的。
路上,苏谧坐在副驾驶位,我和徐总坐在后排。徐总在打电话,我的视线越过车座,对上前窗镜里苏谧的眼睛,那双眼照例看不出情绪的痕迹。
我时常猜测苏谧在人后是否也有放松的一面……也许在家里穿着居家服喝啤酒、吃外卖烧烤;也许躺在床上玩一会儿手机游戏,不小心手滑被屏幕拍了脸;也许,像所有同龄人一样,坐在桌前对着电脑播放的成人影片自慰,纸巾盒摆在触手可及的位置。但这些日常画面都很难代入苏谧的脸——那张从来没有笑容的、石像一样的脸。
初见苏谧的人可能会被他冷淡面孔吓到;相处久了就知道,他只是缺乏表情,不是冷血。他会事无巨细地指导手下的新人,我也曾被这副冷淡外表下的关照所打动。这样说应该不算夸张:苏谧是个非常温柔的前辈。而他对徐总,又不仅仅是温柔,简直是ai管家一样的准确无误,照顾着徐总行程中的每个细节——包括今晚这一类余兴节目。出国在外,基本的联络工作都是苏谧在做。
徐总不会什么外语,别说外语,拼音字母都写不全。但他身上有一种离奇的自信,前些年一个人闯荡国外也能不可思议地畅行无阻;像很多成功生意人一样,他有交朋友的天赋,用简单话术说服他人的奇异魔法——同样的话由我说出来绝对不会奏效。能成功的人总归有些天助,而他身边还有苏谧这个得力下属。
我们的车很快到了目的地,一个斯拉夫长相的男人带了几个侍者装扮的青年男女,在停车场迎候我们,苏谧叫他“扬科”,口音听不出是哪国人。苏谧和他说了几句,回头对徐总说:“扬科有个惊喜给你。”
听从店主的安排,我们没有从正门进店,对于那里面的光彩和喧哗只有远远的一点感知。扬科带我们走下几道装潢精美的楼梯,在一间地下套房外停下,要求我们把手机锁进储物柜里,这扇门内禁止拍摄或联络外界。我对此有些不安,但苏谧和徐总都习以为常似的照做了,我也不好抗拒。
套房里有一片宽敞的招待区和两扇通往内间的门,这里很安静,完全听不到地面上会所大厅的热闹。
音乐和酒水来到的同时,扬科的手下人带进来一个金发年轻人,乍看是个胸部发育不良的女孩,细看之下才注意到手脚骨节的形状和胯下不太明显的包裹。那是个穿着白色比基尼装的男孩子,及腰长的金发微微卷曲着,包围着他细瘦的身体。
那孩子看上去很小,最多十六七岁。我知道,如果我开口质问,扬科或他手下人一定会保证说这是成年合法的工作者。在他人地界,最好还是闭嘴少生事端。
至于徐总,我没听到过关于他是同性恋或者别的什么的传闻。我陪他去过普通的风俗场所,洗头,按摩,唱歌,他对女性服务者的态度和其他在这类场所消费的男人没有两样——欣然接受夜场女性的抚慰,没有过抗拒的意思。
不过,眼前这个孩子,大概也不能算是男同性恋的口味,瓷人偶一样的精致面孔,更像是一种无性别的存在。扬科叫他“尤莉亚”,看来是当作女孩售卖的,这印证了我的猜想。跨性别女孩或异装男孩,本来就在直男的取向范围吧。
杨科打了个手势,尤莉亚顺从地走过来,踩上我们面前的窄小桌台上,翩然起舞。他在距我们一臂之外的空间舞动自己,但手脚轻盈灵巧,不会撞到任何一位看客。
当然这不是什么才艺展示。只是让消费者更清楚地看到这玩物身上的每一寸白嫩皮肉。隔着绷紧的、半透明的胸衣,我们看得到他双侧乳环的金属色泽。
尤莉亚似乎明白我和苏谧只是随从,并不关注我们的反应,目光只投给坐在中间的徐总。
扬科说他在老家是个芭蕾学生,舞跳得一般,没什么前途,家里也没钱继续供他,就辍学来这边打工了。苏谧平静地听着,一一翻译给徐总。
从他优雅的动作中还能看出学舞的痕迹,但过于纤细的身体显然是荒废练习的后果,以他现在的体型,恐怕不能完成一个合乎标准的“猫跳”。他好像听不懂德语或英语,又或是他的老板不准他和外人说话——也许他的声音不像外表一样中性化,会打破这完美幻想,让老徐这种并不自认为同性恋的客人扫兴。
徐总目不转睛地看着那个男孩。看得出来,他对这份招待相当满意。
尤莉亚对着他的新客人摆动腰身,藏在白色小裤里男性轮廓在他向前顶胯时显得更为鲜明。他诱惑观者的动作很流畅,脸上没有表情,嘴唇偶尔紧张地开启又闭上——像那种初入工作场合的新人万分害怕犯错的样子。他的双手在自己身上游走,隔着那一点点衣裤机械地抚摸下身和乳头。
老徐伸手捞住那孩子的细腰,顺势剥开他的胸衣,扯动一侧乳环。令我们意外的是,尤莉亚惊恐地挣脱搂抱向后退开,像个遭到侵犯的女孩一样用手臂掩住胸部,发出奇怪的呜咽。
我从没听过这样的声音,有点像自闭症儿童遭遇不当刺激时的喊叫。也许这孩子精神不正常;或者扬科禁止他说话,他只能用这种粗暴方式进行有限的表达。
扬科身边的人对苏谧说了什么,苏谧转告徐总:“尤莉亚很害羞的,不要在这么多人面前搞他。”
他们又低声交谈了几句,扬科似乎被说服了,带着他的卒子们离开了套房。我猜多半是徐总同意支付和尤莉亚独处的价码。那么所谓的“害羞”也只是演戏吧,作为整套服务的一部分……?
扬科走后,我们——确切地说,是徐总——可以对尤莉亚为所欲为了。
苏谧跷着腿坐在一旁,视线垂向自己的手指,百无聊赖的样子,像那种在商场休息区等待太太购物归来的已婚男士。说起来,我不知道苏谧是否有家室,他从不谈论私人话题。显然,尤莉亚没有在他身上激起丝毫欲望,但我不会把原因归结为他是个“正常男人”,他不是,无论什么性取向,他绝对不是个正常人。一脸淡漠地陪同老板嫖妓,这已经不能算是正常表现了……亏得徐总不嫌他扫兴。
也许我没有资格嘲讽他,我自己的表现恐怕也称不上得体。房间里只剩下我们和尤莉亚,我感到很不自在。如果是有一群姑娘作陪的场合,我可以随便亲近其中一个,轻易融入场景里,但眼下这个情形,我不知道该做什么。老徐自然要和尤莉亚发生点什么,我在这里又有什么意思?我不想成为苏谧那样煞风景的存在,也怕老板不会像对苏谧一样允许我扫兴。
更让我不安的是,我在尤莉亚眼里看到了恐惧和抗拒。
这孩子真的是个性工作者?或者……
也许是迫不得已,像一些廉价色情读物里的故事那样,为还债之类的理由堕入风尘?也许……我想到更残酷的可能性,人口贩卖和强迫卖淫。
尽管没有凭据,我总觉得有些什么信号在告诉我:尤莉亚不是自愿的。
我试图在他身上找到线索。我知道很多黑道经营者会用药物控制他们买来的“货品”。但尤莉亚的手臂和大腿上没有针孔,眼神也很清亮。也许就连不法商人都不忍心让药物毁坏这天造地设的美貌。
徐总再次揽住尤莉亚,摸到那双白腿中间,揉搓那一团并不惹眼的坠物。他动手解开三角式下衣的绑带,让那小衣物掉落在男孩的白皙双脚之间。
尤莉亚终于完全赤裸了。他的性器很小,不是残疾或发育不全,只是很细小,像文艺复兴时期雕塑家崇尚的美学,一小片金色茸毛覆盖着器官上方的皮肤。
老徐一手拢住尤莉亚的私处,像爱抚小动物那样,漫无目的地玩弄它们。男孩的身体在他手下颤抖,被抚摸的雏鸟没有抬头。我听说过那种调教,让男孩子长时间戴着贞操锁,直到他们难以勃起,只能用后面获得快感,被插入时会给出更好的反应。
尤莉亚抬起手,像是鼓起了极大勇气,怯怯地牵动徐总的衣袖,看样子是请客人跟他进里间卧室去做。也许扬科说的不完全是谎话,我确实感觉到:他不想被我和苏谧围观。
但老徐不买账,执意在外面享用这道美味。他反握住尤莉亚的手腕,推到沙发上。他没有浪费工夫用尤莉亚听不懂的语言解释,只是按住那孩子头颈,迫使他跪趴在宽厚的沙发垫上,让他湿漉漉的小洞暴露在我们面前。不必插入手指验证,这润泽发亮的洞口一看就是好好准备过的。
苏谧从手包里摸出安全套,递给徐总。他知道徐总所有的偏好。他为徐总准备烟酒、服饰、餐点、预约场地,但我没想到就连这种东西他也有特意安排。我的眼光扫过落在地上的安全套包装,猜想这是否也是苏谧自己偏爱的一款……如果他真有性生活,一定那种坚持要戴套的类型吧?
苏谧长得不丑,有一张虽然无趣但也算得上清秀的脸。当然比不上尤莉亚这样雌雄莫辨的美,但有他自己的……味道。如果他想要一个床伴,应该不是难事。